清明回乡,我发现村里欠了爷爷百万赊账单。
原本只想追回债务,却意外被乡亲们塞了个“村长”的头衔。
“这年头,谁讨债谁当家!”
老乡们振振有词。
本想连夜跑回城,村口老槐树下竟摆开说理阵仗。
九十岁的太公敲着烟袋:“钱,村里是还不上了。”
“但我们可以还人——把我曾孙女许配给你!”
望着不远处那位硕士毕业的回村女医生,我陷入了沉思。
---清明时节的雨,细如牛毛,把陈家坳裹在一层湿漉漉的灰纱里。
陈默开着那辆满是泥点的SUV,碾过山路上最后一段坑洼,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。
槐树更老了,枝干虬结,新芽还未爆出,沉默地俯瞰着这个同样沉默的村庄。
空气里有新翻泥土的腥气,和雨水的清冷。
村里比记忆里更静了些,青壮年的背影少见,偶有几个老人坐在屋檐下,看着雨丝发呆,眼神浑浊,直到认出陈默的车牌,才微微亮起一点光,拖着长音招呼:“默娃子……回来啦?”
“哎,回来了,叔公好。”
陈默摇下车窗,应着。
车窗外的村委办公楼,墙皮剥落得厉害,露出里面深浅不一的砖色。
他是回来给爷爷上坟的。
老爷子去年冬天走的,没熬过那个酷寒。
忙完后事,陈默整理爷爷那间临河小药房的遗物,在一口老樟木箱子最底下,翻出了一本厚厚的、纸页泛黄发脆的账本。
封面上是爷爷一笔一划写的“乡亲药费赊账录”。
翻开,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三十年来的赊账:谁家,何时,因何病,取了什么药,值多少钱。
一笔笔,清晰又沉重。
陈默花了几个晚上,用计算器逐条累加,数字最终停在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位置——一百零七万八千四百二十六元整。
许多名字后,用红笔轻轻划了一道杠,那是爷爷表示已还清的记号。
但这样的红杠,太少。
更多的是空白。
他这次回来,除了给爷爷磕头,心底还压着这件事。
一百万,不是小数目。
爷爷一生仁心,几乎白送药看病,临了只剩这本沉甸甸的“情义”。
父亲早逝,他是长孙,这债,他不知该不该讨,如何讨。
上过坟,烧了纸,看着青烟混入雨雾,陈默心里堵得慌。
他在村里转了转,最终拐进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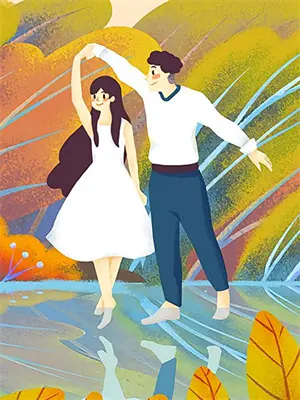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